按语
本学期,21级本科新闻和20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2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我们的家乡到处都是大山、泥土、农田和牲畜。我们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老老实实地守着土地或者外出打工。他们不懂职业规划也提供不了帮助,好好学习走出农村是我们一开始的宿命。”
当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来到城市学习、工作,他们希冀能拥有更加丰富精彩的生活,却发现现实世界的残酷。“我们见识了很多,心态和生活都在城市化,根基却是乡土的,在迷茫、焦虑、自卑等情绪的冲击下,常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只不过,我们还是认真学习,常常思考。不论以后是在城市奋斗,还是回到农村、小镇、县城,我们都希望能够过好这一生。”
46766个用户在豆瓣“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小组聚集。当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广布,仍有这样一批难以被忽视的群体——农村大学生,在一二十年的成长历程中逾越一道道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障碍,不断突围,不断向前。
“山里飞出了金凤凰”
2012年,瑶瑶正上高二,村里收到了贫困县拨款,开始修起了水泥路。一条连接村庄各家、崎岖蜿蜒的泥泞小道,在2013年5月份正式竣工,摇身变成了一条平整宽阔的水泥大道。高考放榜日,一条轰炸性消息便随路上闲谈的村民不胫而走:“今年村里有三个女娃娃考上大学!三只金凤凰啊,真了不得!”
瑶瑶正是三只“金凤凰”其中之一。她如愿被一所江苏省的一本院校录取,同村的另两个女孩也考上了省内的二本大学,只不过,相较于以往,这是破天荒的特例。面对父母的笑容、乡亲的夸奖,瑶瑶一开始也同样是激动而兴奋的,“金凤凰”的名头恰恰是她寒窗苦读的硕果。然而,渐渐地,村里皆如此评论——“正是因为修路积攒福分,今年才能有三个大学生啊!”“明明是我自己努力读书,怎么就成为了修路的福报呢?”瑶瑶愈发觉得郁闷。
2018年,金松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院校的大学生。“你这儿子不应该叫金松,而是一条从山沟沟里飞出去的金龙呀!”得知消息后劳作于田间的乡邻们口口相传。村里的主任、镇上的书记都对他进行了嘉奖,金松一共拿到了五千块钱的奖励金。金松的父母对于分数并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考上一本大学是一件厉害的喜事,逢人就夸奖自己的儿子,在庄稼人的世界里感到一番扬眉吐气。然而,只有金松自己知道,自己并不满意考试结果,距离理想大学差了几十分,可面对亲戚们的恭维、父母的欢欣,金松只能再三缄默。“在村里没有人能理解我,如果我说没考好,他们可能会认为我考上大学还不知足,是在炫耀。”金松认为,考上一所普通大学,在城市里、小镇上都只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但在自己的村子里却多年难得一见,这让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

(金松家门口可见的山田)
2021年6月25日,可以查询到高考成绩的当日早上,不少亲戚便打来电话关切燕冰的考试情况。从小到大,燕冰的成绩保持优异,一路从村镇小学考到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是众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村镇里便对燕冰的高考寄予了厚望。“你听说了吗?老李家的女儿考到北大是差不离的事了,太给咱们村争脸了!”学校里可信的消息一出,燕冰的高考成绩即被纷纷称赞。但乡邻们不甚了解的是,燕冰在高考前填报了北大的农村专项计划并成功通过,这才得到了预选名额,意味着高考成绩只要在省内同样填报了北大农村专项的学生中排名第一即可,在与拥有农村户口的优秀学生之竞争中实现所谓“降分录取”。如若没有农村专项计划,燕冰的分数能录取到人大,但燕冰在填报志愿时选择更上一层楼,最终上岸了乡亲们认知里“中国两大最高学府之一”。面对这样的结果,她的第一直感仍是幸运。
可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农村大祠堂拉红幅办完升学宴之后,燕冰开始感到担忧与焦虑。她常常在夜里想自己配不配得上北大,“自己毕竟是小地方出身,考上了北大开心又惶恐,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金凤凰,在北大里,我应该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开学前我还常常害怕自己太差劲、太落后。”回想起自己考上大学的历程,燕冰只感到:“一路走来,感觉真的很神奇。”
“寒门”如何出“贵子”
“人生抽到这样的开局,是很不容易的,别人开始就爆出一个武力值顶配的宝剑,我嘛,只有锄头。”金松的家就在山上,整个村子大约有五十家住户,除了隔几十步能走到一处邻居家,四周皆是茫茫的绿野山田。金松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田里活少的时候,我爸会去工地上搬砖,起初一天只有二三十块钱,后来一天能挣到一百多。我妈在家里种田养鸡,农闲的时候再和我爸一起去搬砖多挣点儿。”父母都在为了生计做苦力奔波,爷爷也要去田里看着,家里时常只留下金松和因患病而行动不便的奶奶。周边又没有与他年纪相近的小伙伴,家里的土墙便成了金松自娱自乐涂抹勾画的天地,他仿着春联和日历挂画,在墙上用不知从哪拾来的粉笔与墨汁炮制出相似的文字图案,土墙就成了金松的第一张字卷,“我爸和村里人看见了,常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写字爱读书的孩子。”

(金松家内贴满奖状的墙壁)
然而,金松小学三年级时,村里的小学因为招生人数太少而关停,为了继续读书,金松每天要独自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镇里的中心小学。为了让父母少操心自己,在升学时,除了县里统一的小升初考试,金松还偷偷参加了一所寄宿制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寄宿制学校主动发来了邀约,并承诺三千元奖学金,父母知道后,便让金松去了寄宿中学。无独有偶,金松的分数本可以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但在中考前夕,学校的领导再次允诺:“只要继续填报本校的高中部,就能有八千块的奖学金。”在金松父母眼里,在哪里读书都一样,当时的金松也认为读书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便放弃在外界看来升学率更好的学校,选择了继续留在这所寄宿制中学。
虽然就读的中学位置也很偏僻,但金松入学后仍会感觉到自己和其他同学间的物质差异,“其他人虽然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但是感觉就自己特别穷。”家境贫寒的叶凡也就读于寄宿中学,同样有类似的感觉。
谈及物质差异,叶凡举出了好几件微小但难忘的事情。譬如初中难得的春游秋游,别的同学都可以带满一书包没见过的新奇零食,自己带的却都是五毛钱一包的辣条。母亲喜欢领免费的广告杯,叶凡曾尝试百遍用笔用刀划去字迹,失败后用一些贴纸遮住广告字样,无奈地使用。高一时,叶凡的同桌带去了一个样式独特的日本品牌保温杯,唤起了叶凡埋藏内心已久的渴望。她用攒了很久的压岁钱买到了杯子的同款。但当她将新杯子给同桌看时,同桌却将自己杯子的商标展露出来,明示品牌和价格的差别。类似的事情发生两三次后,叶凡越来越沉默,对金钱和家庭条件也更加敏感。

(叶凡后来购买的正品保温杯)
相对其他同学优越的家庭环境,金松和叶凡心里都感到总有种强烈的羡慕之情。虽然物质条件没办法齐同,金松和叶凡却有相似的决心——“那就在学习成绩上领先别人”。中学时的金松认为:“只要我够努力,成绩也可以追上好高中的学生”,他便挑灯夜读,总是在宿舍统一熄灯之后还在自己的小床上亮起小夜灯刷题。叶凡则抱着一个原始的朴素愿望:“只要我成绩够好,我以后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她总是班级里到得最早的一个,看着桌上自己刻下的一句最喜欢的句子“我来人间一趟,我要看看太阳”,而后开启新的一天。
燕冰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到燕冰出生的时候,父母落点在广东开一家小超市。在广东读完三年级之后,父母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业,燕冰便回到了福建老家,课后上托管班做作业,平时则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成了留守儿童。爸爸妈妈每年回来一两次,寒暑假有空燕冰再去找他们,除了隐隐约约觉得自家经济条件差些,在平时与同学们的相处中,燕冰更多感到父母陪伴的时间差异。她将广州的中山大学定为自己的目标,想离爸爸妈妈更近一点。偶尔有一次考试不理想,燕冰都会闷闷不乐,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对考试非常畏惧。高三的时候,燕冰选择留在学校寄宿,只为摒除干扰,减少通勤时间。她和同寝一个离家甚远的女生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度过了最后一段艰难的苦读时光。
随着年纪的增长,瑶瑶越来越觉得“世道不公”。迷信的观念、稀缺的见识、失误的决策,是村子贫穷与愚昧的根源。瑶瑶深刻体会到村里浓厚的重男轻女传统观对自己的影响。身为家中长女,瑶瑶从小就被教育“穷人家的大孩子早当家”,不许和弟弟争,虽然十几年来行动如此,她也真心实意地爱护着弟妹,但瑶瑶始终不甘心。瑶瑶最讨厌弟弟爱唱的“爱我你就抱抱我”儿歌,有了妹妹和弟弟之后,爸爸妈妈再也没有一心一意地抱过自己,也没怎么夸过她。看到父母听到弟弟唱歌后的笑容,瑶瑶内心涌动着失落。“都说学习改变命运,我当时就觉得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考出去,让父母刮目相看,去外面找到自己的价值,否则我觉得我将来也会成为种田生儿子的农家妇女。”不愿囿困在潜藏隐性规则的村庄里,瑶瑶十分注重自己的学习成绩。对瑶瑶而言,考上大学,是改变生活的唯一出路。
在小樱所居住的农村里,小樱一家只有她和姐姐两个女儿,无疑是种“特殊”。常有老人劝说小樱的妈妈再生个儿子,“等到看我妈真的没有再生育的想法了,又过来说我家没有延续香火的后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小樱想要证明给周围的人看,女儿也能大有出息。于是,小樱成了村里唯一一个从乡村小学考到镇中学,又考进县中学火箭班的新生代。身边的同学有中途辍学的,有早恋早婚的,也有不专心读书最后上了职专与大学渐行渐远的,但小樱坚持下来了。
“考上更好的学校之后,我也有了很多新朋友,身边的同学都在很认真地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我的求知欲和梦想也越来越大”。“因为我的名字里带樱,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武大梦,后来高考虽然发挥得中规中矩,上了南京的一个211,但我发现,有樱花的地方非常多,南京也很好,还有很多漂亮的银杏树。”对小樱来说,虽然求学的过程很辛苦,整日刷题苦背,要为了每次的考试排名而食不知味,但历尽千帆,学习的压力也是动力,她坚信熬过了“寒窗苦读十余载”,会有绚丽多彩的大学生活留待自己去探索。

(小樱喜欢的校园银杏树)
不同的缘由与初衷,然而同样的路径都是“一本书读到烂”。面对老旧的教学设施、匮乏的教学资源、鲜少的学习机会,农村学子们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刷题念书刷题,提高成绩,这是“寒门贵子”各异又相似的漫漫求学路。
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
“原以为考进了大学,大家就能差不多在一条水平线上了,但是除了家境,实际上我们自身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差距。”大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学生脱离了试卷高高摞起的书桌,开始展露自己鲜活灿烂的青春。
拿到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通知书,燕冰本以为自己可能会有点不如“各省的顶尖强手”,但依旧可以在大学顺风顺水。然而,当面对周围同学各式各样的竞赛经历和奖杯证书,燕冰曾经因为成绩优异而拥有的光环也在逐步崩解。
大学第一节英语课上,同学们需要用英语做自我介绍,燕冰略带口音的蹩脚英语极其突兀。计算机课中,她看着旁边同学熟练地敲击着键盘,自己则第一次接触编程,从零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当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国各地旅游沿途的风景时,只往来过闽粤两省的她只能尴尬地坐在一旁,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
“井底之蛙。”燕冰这样评价自己。
2022年,“小镇做题家”这个流行词语随娱乐新闻再度火爆,燕冰与之产生极大的共鸣,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这不就是我嘛。”燕冰自嘲一笑。燕冰最喜欢的诗人是王尔德,她时常带着一本诗集,在未名湖畔念诗,放空焦虑的自我。“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燕冰常来的湖塔边)
小樱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后,第一感受是自己就像丑小鸭误入了天鹅群。江苏地区的同学都多才多艺,自我介绍时会滑板、唱歌、跳舞、朗诵,各种各样的技能展示让小樱有了一种“天花乱坠”之感。在同学们的各色耀眼光环下,她在和同伴及老师打交道时,总是十分紧张,小心翼翼斟酌着措辞。在一次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报告比赛中,小樱拿到了最高分,拥有去参加校级评比的资格。面对如此珍贵的机会,她却犹豫了。“我不想上台演讲。”敏感拧巴的她不愿意暴露在同学们的眼神下,在辗转反侧几天后,小樱选择了放弃。当告诉老师自己的决定后,没有不甘,小樱反倒有种如释重负之感,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喜悦。
国庆假期,小樱在学校旁边的商场得到了第一份兼职。她穿着统一工服,站在金店门口,为进店的顾客分发小礼物。不停的微笑让她脸部酸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小樱浏览微信朋友圈时看到了同龄人们都在外出游在,自己也“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旅游软件,查询离南京较近的扬州旅游地费用——七十块钱的汽车票是她几近四天的伙食费。“最后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没有出去肆意玩的资本,还是好好做兼职吧。”
小樱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一千元,她主要的购物消费平台是拼多多,东西便宜,性价比高。每个学期,她都会在拼多多上买一箱自己最爱的牛奶,唯一一次破例是蒙牛新推出一款草莓味的牛奶,18.9元20盒的真果粒,纠结了好久,小樱最终咬牙买了一箱。她还曾看中一对8元的耳饰,每天都会打开收藏夹欣赏样图。然而,在收藏两个礼拜后,这对耳夹下架了,小樱在拼多多上搜索同款,没想到却比原来更贵。“我最后还是下单了,但花了12.9元,它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面,只有正式场合我才戴几次。”


(小樱的网购订单)
瑶瑶刚进入大学后,室友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她从未听说过的MINISO、三福、屈臣氏,而自己却完全听不懂,也没有勇气询问这些新词是什么,只能在旁边默默收拾着床铺。刚进入大学的女孩子们如同初绽的花骨朵,青涩地释放自己的美丽。看着室友们人手一套化妆品,相互交流化妆经验,瑶瑶只觉得跟她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代沟。“不正经的女生才化妆打扮。”在村子里长大的瑶瑶,在父辈们耳提面命下,从小接受的观念开始出现裂痕。在生活里的其他方面,她也闹出过不少笑话,第一次宿舍聚餐便以不愉快的吵架收尾。结账时,瑶瑶认为应该吃多少付多少,自己没有品尝的菜品她不会付钱,这与秉持AA观念的室友们发生极大的冲突。“现在想想自己当时挺傻的,一起吃饭大家AA就好了,可当时我对钱特别看重,就是认为自己不该为没吃的菜付钱。”
2022年6月,疫情爆发后,叶凡回到了衢州农村在家上网课,课程期末考试也改为线上,要求全程打开摄像头。但当叶凡凝视着自己的房间,淡淡的抗拒却涌上心头。叶凡的书桌是家里十几年前淘汰的一张大餐桌,表面的漆已经脱落,露出斑驳的木头原色。叶凡的床是几年前亲戚不要的木头床,铺着大红花纹的床垫,年代感十足。考试前,她把自己的床用被子铺开遮住,调整摄像头的距离,让其刚好能看到自己的半身,不会露出房间其他地方。“就是不好意思,害怕大家看到我的房间。”
农村学子初入大学,往往会受贫穷的经济条件、线性的思维方式、浅薄的见识经验、稀缺的才艺技能、自卑的心态心理所限,面对全新的世界、光鲜亮丽的朋辈而手足无措。十几年时光专注于应试教育,其他方面无异于一张白纸,走出闭塞的乡村,“小镇做题家”们的大学之路才刚刚启程……
大学:悦纳自我的新起点
叶凡小时候,母亲就一直强调家里的贫穷,加之同龄人若隐若现的优越感,攀比事件发生几次后,叶凡越来越沉默,也逐渐养成了对钱极其敏感的性格。时隔十几年,连母亲都忘记曾经借过某位亲戚的钱,叶凡依旧能念念不忘。
幸而,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叶凡遇到了一些乐于接受自己的朋友,在朋友的安慰与温暖下,叶凡可以轻松的将自己以前羞于表达的“穷酸事”讲出来。如今的她,将自己放在旁观者的角色,不再固执地和别人比较。她会冷静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并想办法去弥补,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燕冰则在北京大学的开放舞台上肆意奔跑着。和身边更优秀的人相处后,她整个人看开了。“现在觉得,如果我因为家庭条件自卑的话,就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她认为,因为家庭条件歧视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对自己出生环境的不满,是对父母的一种轻视。大学给燕冰带来了更多自信,燕冰更愿意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人际交往中也更加从容,依照自己的交友倾向构筑恰到好处的舒适圈,曾经偶尔会逃避懒散的性格也有所改善。
课外之余,小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尝试加上自己喜欢的专业课老师的联系方式,主动和同学打招呼,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她加入了学校文博义工社,去南京博物馆做讲解,也组织策划了一些志愿者活动,帮助陪伴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尝试用自己微弱的光芒温暖别人。
大一的暑假,小樱没有回到家乡,选择留在南京实习。“底薪一个月两千五,还有绩效提成。”小樱不想继续读研,想早点工作减轻父母的负担,便尽早涉足自己的专业——广告行业,尝试体验实习就业。暑期两个月下来,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小樱还剩余一千多元,她开心地给父母发了大红包。“我可以养活自己了,也能改善家人的生活。我和我姐姐也能很好地孝顺父母,也能成为他们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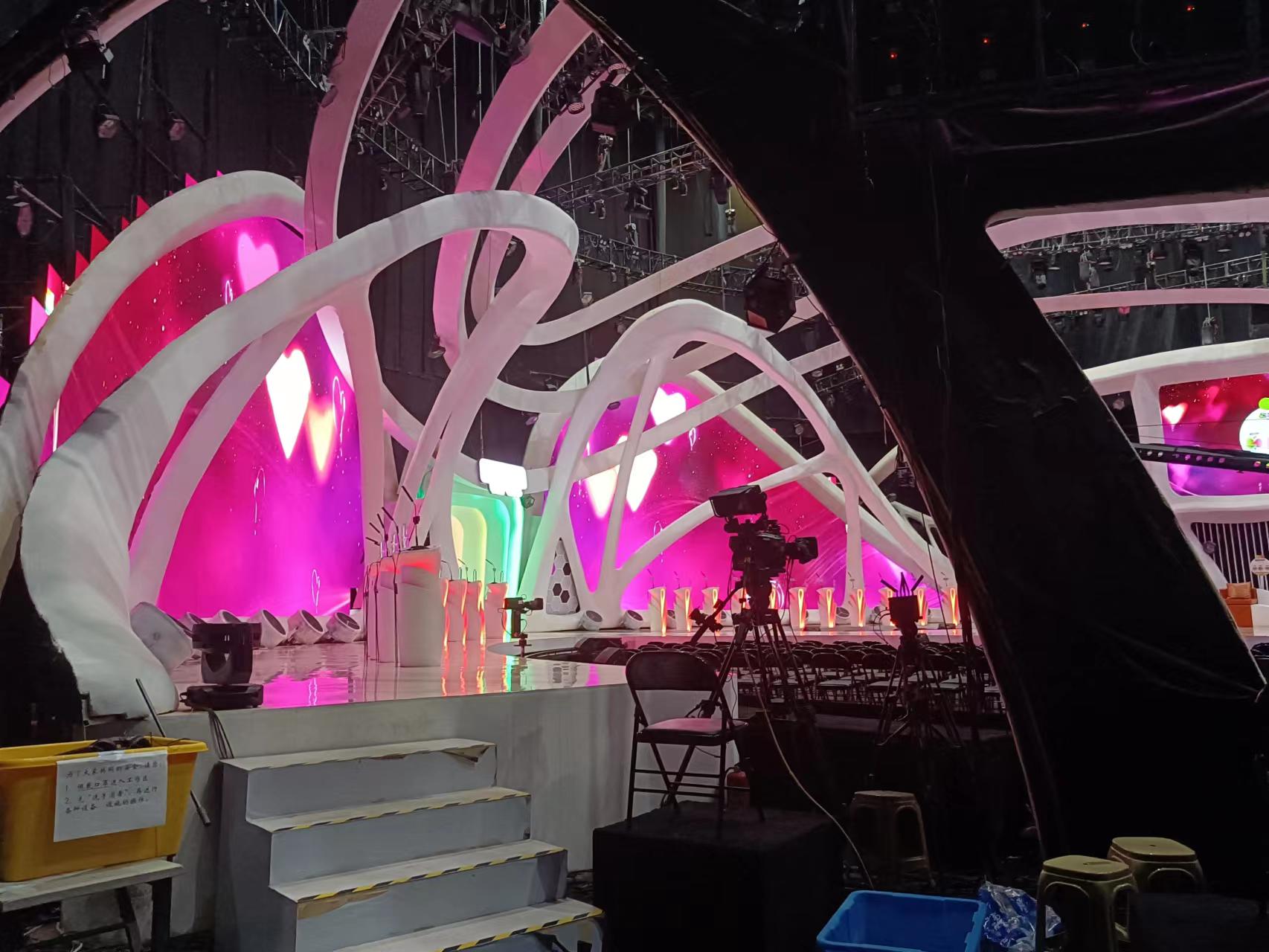
(小樱暑期实习的外出工作照)
刚进入大学时彷徨无措,金松便默默埋首学业,仍旧用成绩让别人记住自己。“刚开始确实会在意别人会不会知道我申领了助学金和家庭困难认定,但是后来也就觉得,要活得恣意首先要悦纳自我,我就是大山出来的农民的孩子。接受平凡才能创造不凡。虽然很心灵鸡汤,但却实实在在地有用。”大学四年里,金松坚持泡图书馆自习,大二敞开心扉加入学生会,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做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的确有人出生在罗马,但是,我走到罗马这一路上的风景,才是我的生命。”2022年7月末,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金松在自己的知乎账号上写下这句话。金松决定继续走下去,迷茫的大雾散去,依稀能见前路光明。
瑶瑶在一次次碰壁中搁置心结、逐渐成长。家里贫困又有三个孩子,父母实属不易,除每月初爸爸给的六百元生活费,瑶瑶还自己承担了两万元的助学贷款,穿着网上淘的几十元钱的衣服鞋子,节俭过日。抓住一切机会,瑶瑶拼了命地兼职、学习,拿奖学金。大学对于瑶瑶来说只是人生的新起点,选择不回归农村家乡的她在上海成为了“沪漂”。“有时候也会想,为什么别人出生就是掌握一手好牌的名门千金,我却不被父母重视,本来以为上了大学就是成功,但一切才刚刚开始”,思忖过后的瑶瑶接受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什么都没有我就靠自己,现在虽然日子还很艰难,但我感觉在步入稳定的正轨。我与目标的距离,是通过自己锚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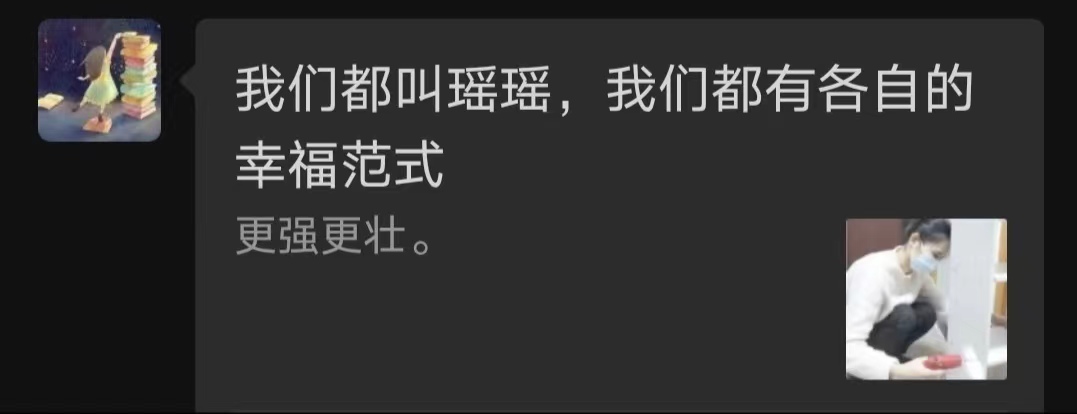
(瑶瑶自己写的公众号文章)
瑶瑶目前做着线上广告投放,工作五年,她已经自己还清了六万元的贷款,时不时还给父母转账、给弟弟妹妹买新衣服。为了招揽客户,也为了自我记录,她在众多社交平台都开设了名叫“我是硬柿子”的账号,更新自己的日常评论与感受。“走出了学生时代,现在的我就像硬柿子一样,不能被随意拿捏。我也期待着自己香甜而醇实的成熟未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瑶瑶、金松、燕冰、叶凡、小樱均为化名)
采写 | 21级新闻学 刘璐 姚思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