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本学期,22级本科新闻和21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3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引语
晚上十点半,是职高教学楼“清场”的时间,熄灯后,小简一个人留在教室,在书桌上支起自己的小台灯,利用微弱的灯光延长一小时的自习时间。一边做题,一边留个心眼观察,只要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她就关掉台灯,躲在角落,等待声音远去。也有“失手”被巡查老师发现的时候,她就假装离开,到楼道避避风头,等老师走后再回来接着看书。有时,抬头一瞥,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也会吓她一跳。
小简觉得自己是在书案前踽踽独行的“笨鸟”,要用这种方式多跑一点才能抵达自己想到的终点。
小简来自河北农村,正在一所职高读高三,在明年的对口高考中考上本科是她目前最大的愿望。
带着对未来的茫然与期许,她凭借有限的认知做着选择,在背离父母与村庄的单行道上跌跌撞撞地前行。
通往大学的路
在考大学这条路上,小简走得举步维艰。
小简并不是一直都在职高就读,她此前所在的县中被调侃为“大专培养基地”——一届两千多个人中,只有两三百人能上公办本科。快到高三时,近三分之一的同学都会选择放弃本科赛道,通过单招升入大专。
高一分科时,小简在知乎和百度上搜寻建议,最后选了物理、化学和政治——小简觉得这是个王牌组合,“既能进中国政法又能学计算机,选专业最广,专业好了给自己创造的就业环境不是一时的。”那时的小简,为自己的未来描画了一张广阔的蓝图。
八十个人一个班,教室里的同学从讲桌下坐到紧贴教室后方的黑板,小简说,“上学是在教室和楼道里摩肩擦踵,就连冬天也感觉不到冷。”小简总坐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防止在站起来听课时挡住身后同学的视线。
然而,想要在高中取得好成绩,对小简来说,并非易事。上课听得懂下课做不出,物理成了最让小简头疼的科目。乡村没有补习班,只有小学学历的父母也无法辅导课业,小简只好在每个课间请物理老师答疑。老师说她学物理努力,而下一次考试,12.5分的物理成绩还是给了她当头一棒。之后她再去问题,老师会直接告诉她,“这个题不适合你做”。
理科成绩差的并不是只有小简一个,升入高二时,班主任开始提醒分低的同学转学文科。文理科分数线差距近年逐渐缩小,抱着文科上线可能性比理科大的想法,小简和其余各个班的82个同学一起转了文科。
在这个班级,小简的成绩从三百多分提升到420分,能拿到全班第四的名次,但她并不开心。
校园里,任何被视作不合群的特质都可能成为恶意的导火索,在小简身上,外貌成了被取笑的理由,而取笑又慢慢演变为辱骂。小简鼻翼右侧有颗黑痣,长期以来,被男孩们视作“丑”的标志。转班后,那些暗地里的指指点点逐渐变成了毫无顾忌的高声议论。评价小简外貌的阵营是慢慢扩大的,最初只有几个同学讨论,久而久之,不参与取笑的男生会被认为对小简有好感,最后,几乎所有男生都加入其中,包括与她有相似经历的、被笑话成“娘娘腔”的那一个。食堂排队时,男生们看到小简会说一句“丑b”,然后笑着绕开,小简尝试过插队,排在她身后的男生会自觉走开,选择其他的窗口。女同学开玩笑说,跟着小简吃饭,就用不着排队了。
嘲笑和孤立愈演愈烈,小简穿衣服被说像“解放前”、梳辫子被说“娘们”、偶然的一句话也能成为令同学们发笑的梗......因为被太多人嘲笑过,只要听到身边有笑声,小简就会下意识认为是在议论自己。一次洗漱时,小简误会了身旁的女生在嘲笑自己,回击了一句“能不能别笑了”,却招来了辱骂,这场闹剧最终以小简的道歉收场。
非暴力的欺凌难以被定性,却在小简的心上扎上了刺,小简在日记里记下那些“仇”,但还是会忍不住在夜里回想起那些难过和委屈,躲在被窝里,她常常想,“语言上的辱骂不算校园欺凌吗?困扰了我这么长时间的事怎么不算?只是偶尔会因为这样的事而悲伤所以就不用管吗?随时间的流逝会自然脱敏吗?”
对小简来说,高中生活是枯燥而痛苦的。她决定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只有戴上耳机听歌时,她才能开心一点。
学校对手机的管控严格,一旦查到带手机进校,就得回家“反省”两周。好景不长,一次在寝室充电时,小简的手机被宿管老师没收了。接下来的两周,小简听话地没去上课,再回学校时,她已经听不懂数学课了。为了尽力把差距补上,小简从早上六点学到凌晨两点,却在白天的课上忍不住睡觉,小简说,自己是个苦学无果的人,那段日子里“一歇就有负罪感,谴责自己,然后继续学,但最后考得还是没人家好”。学校按照名次分班的时间将近,她看着不理想的成绩,开始担心下一次分班的结果,更担心因为去不到好的班级而无缘本科。
当职高老师来做招生宣传时,小简得知了农村户口读职高不需要学费,虽然只能上本省的学校,但对口高考更容易上本科,她又找到了新的方向。
今年四月,小简转学到了职高。当她从妈妈的电瓶车后座走下,拎着两个沉甸甸的编织袋踏进职高校门时,她觉得自己离大学更近了一步。
可供选择的专业有限,小简学了会计专业,因为听说会计好就业。新班级只有23个人,都是想要争取考上本科而从普高转入职高的。然而职高的学习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早上六点二十到晚上十点,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压力并不小,不少同学都曾因为坚持不下去而纠结是否转向单招。分提不上去的时候,小简也会想要放弃,她数过,最多的时候自己一天叹过27次气。专科院校的老师来班里发传单,小简也拿了一张,但上面五位数的学费使她彻底打消了动摇的念头,她知道,家里没办法负担这笔高昂的学费。
在这条蜿蜒曲折的路上,没有人为她指明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也没有人告诉她前路是否崎岖,靠着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小简独自摸索着向前,从一个岔路口拐入另一个岔路口,方向飘忽、时快时慢,她始终明确的,只有这条路的尽头,那个名为“大学”的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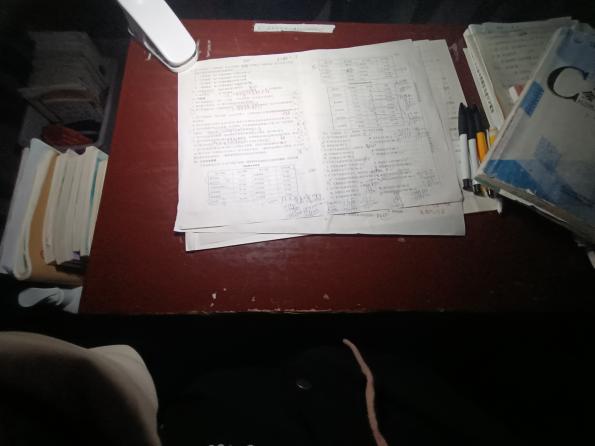
熄灯后,小简独自在教室里学习
想要离开的家
小简的手机被老师发现时,是妈妈来学校接的小简。坐在电瓶车上,妈妈责怪小简丢了自己的脸。
小简说,“妈妈好面子,怕丢脸,一生都在做农村人刻板印象中的好女人。”
小简的妈妈只读完了小学。升学时家里盖房,正好赶上了缺钱的时候,有限的资金需要用于供弟弟妹妹上学,小学毕业后,身为长姐的妈妈就听姥姥的话,辍了学,回家分担家务和农活,再大一些就出去打工。
妈妈二十一岁那年,有了媒人上门,姥姥认为两家的经济条件门当户对,就收下六七千的彩礼,做好了家具送去当嫁妆,早早地把女儿嫁了出去。村里的女人一旦成家,就被赋予了传宗接代的使命,生不出儿子就是“没了后人”“断了血脉”,于是,结婚后的几年,小简妈妈的生活围绕着家务、生育和哺乳展开,在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孩之后,家中终于顺利诞下了男婴,小简妈妈的生育历程也以节育环划上句号。
小简的爸爸在工厂做搬货卸货的体力活,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抚养四个孩子的经济重担压在肩头,爸爸常说,“养孩子太苦了”,他缓解苦痛的方式就是酗酒。有时是和工友一起在路边的烧烤摊喝,有时是自己买了酒回家喝,而他醉酒的日子,就是家里人的“受难日”。爸爸总在一番抱怨后,对着家里其余五口人拳打脚踢。
小简常常被打,干重体力活的人力气大,巴掌扇到脸上不久就发红。最激烈的一次争执中,小简被爸爸猛地推向地面,妈妈在身后及时接住了她,随后自己却被推倒在墙边的尿盆里,头发上沾满了骚臭的尿液。半夜十二点,小简哭着拨通了110,叫着要把爸爸送进派出所,电话那头的人劝小简,“哪有家长不打孩子的,送进去了你吃什么喝什么”,小简止不住哭泣,没能再应答,对方留下一句“有事去找大队”后,电话挂断了。
小简的妈妈想要出走,想回娘家住,想就此离婚。她带着四个孩子出了门,走到桥上,她甚至想纵身一跃,一死了之,但身后的四个孩子不能没了妈。没钱、没车,走不远,去亲戚家睡了一宿后,四个孩子还是和妈妈一起回了家。
之后爸妈吵架时,小简再提起离婚的事,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别上学了,代替你妈妈,负责在家洗衣做饭。”小简说,“那一刻突然感觉生活的重担压在了自己身上。”
现在,小简的妈妈在工厂做着用机床加工螺丝的工作,一天拿七八十的工资。而小简作为家中的长姐,则要在每次放假回家时负责包揽家里的大部分家务,“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当的是家务的家。”小简常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就回到妈妈辍学那年,拉着妈妈半工半读,挣了学费后好好上学、好好工作,经济独立后再自由选择结婚与否。
小简知道爸爸养家辛苦,厂里的活一来就得“死命干”,有时候需要连续工作二十几个小时。小简也知道妈妈收入不高,没办法独立养活四个孩子。但她并不认为妈妈理应有这样的家庭和命运,她只觉得姥姥残忍,恨姥姥没让妈妈再上学,恨姥姥早早地就让妈妈嫁人,生下那么多孩子,遭受那么多苦难。有时,妈妈也会羡慕那些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孩们,而自己当年如果不结婚不生儿子,会招来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
小简说,“我不想过和妈妈一样的生活,我就想适应社会的规则,考个好大学,然后离开家。”她期望能够摆脱过去背负在父母身上的枷锁,步入乡土之外的社会,而读书是她充满变数的人生里唯一能把握的确定,无论前路坎坷与否,她都愿意继续走下去。对她来说,要想突破家庭的禁锢,除了读书,她再无选择。

在家里,小简最喜欢的是两年前捡回来的流浪狗
未来
小简的名字里有个简字,书简的简,因为妈妈自己没能多读书,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而现在,妈妈好像没那么希望小简读书了。
以前的同学有不少辍学打工的,做幼师的、看门市的、端盘子的、进电子厂的、当收银员的,妈妈常和小简念叨他们自食其力的事。爸爸也常常撺掇,“我都上个小学毕业,你上个高中算好的了,我看你也考不上,不如现在就去打工”,小简不愿就此妥协,“我想努力读书,不想后悔。”
中考前,小简也曾以为自己考不上高中,和好朋友做好了以后去做美容美发或者通下水道的准备。中考后,好朋友没能考上普高,去读了职高,又因为不愿忍受欺凌,辍学回了家;而小简升学后,考上本科成了她最大的愿望。
其实小简也去“工作”过,那时小简四岁,还在姥姥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学。每天下午放学,姥姥来幼儿园接小简,牵着小简的手,一起去工厂。小简把简易的厂房称作“白色的长方体”,厂子里都是女人,年老的已经当了婆婆,年轻的刚做妈妈不久,她们的工作就是把膨胀螺栓的螺母拧上,按照拧的螺母数量计算工钱。小简在这里学着女人们的样子拧螺母,困了就躺在一兜兜还未组装的零件堆成的小山上睡觉。她的工作成果算在姥姥的工钱里,数量多的时候,一天能拿到三十。小简说,后来,姥姥拧螺丝攒下的钱,给大舅舅出了首付,给小舅舅开了门市。直到现在,七十二岁的姥姥依旧每天四五点起床,七点就到工厂里拧膨胀螺栓。
暑假时,大妹妹听说班上的同学在螺丝厂做兼职,也向小简提议打工赚钱。找妈妈要来了本地求职的网址后,姐妹俩守在手机前,由妹妹筛选合适的岗位,小简则负责拨通电话。很多岗位都是已经停止招工但还未删帖,打了十几个电话后,只剩下一个电子厂、一个超市收银员和一个外卖员的岗位还有空缺,最后也因为假期时间太短没能谈妥。
但小简绝不想和妈妈一样,一辈子留在本地,打简单的零工。她听老师说过坐高铁很方便,也想自己试试高铁有多好。她看过班上家境好的女同学旅游时拍的照片,也想去苏州、去上海、去乌镇,自己看看江南的美景。
小简喜欢上网,喜欢在网络上看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截然不同的人的人生。她说,“我读书少,见识少,体验的太少,要通过网络来认识社会。”小简的手机是网课时买的,6.5英寸的一方屏幕,成了小简了解远处世界唯一的窗。
小简看李雪琴的同学“在下辉子”的《高考同学盲盒》系列视频,这个全班985、囊括当地省状元的班级,在小简看来,是自己“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看得清差距,“资源不一样,能达到的高度也不能按一样的标准去衡量,所以我考个二本就很厉害了”。她也看那些“05后宝妈”记录生活的视频,为她们的人生感到悲哀,“我们只是在正确的时间知道了正确的事,她们不知道,我还能读书,比她们好太多了。”
去年冬天,小简刷到了《半边天》节目中刘小样的采访视频,也知道了她那句“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小简把刘小样视作一个觉醒的女人,“在农村,这样觉醒的女人太少了,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清醒就好了”,她希望每个女人都能像刘小样一样,拥有向往自由的权利。她学着刘小样的句式,把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描述改成了:“对于我家: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对于学习:我宁愿麻木,我不要痛苦。”短短两行字,是她对现状最深的感受。她一遍一遍地提醒自己,要靠读书改变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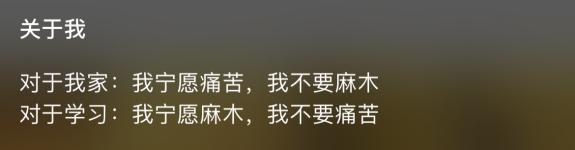
小简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描述
小简出过一次河北,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和姥姥姥爷一起坐绿皮火车去了北京的小姨家。每隔一段时间,小简就会从脑海里翻出那段对大城市唯一的记忆,“故宫有好多白楼梯,和古装剧里的一模一样;但是出租屋里的天花板太压抑了,我还是更喜欢高房顶;还喝了小姨家的葡萄酒,我是小孩胃,喝不惯,总感觉是苦的。”
但她还是想去大城市。六月高考结束后,小简打算再去北京找一次小姨,再逛逛北京的其他景点,弥补三年级时没看到天安门的遗憾。她还想利用暑假剩下的时间送外卖赚钱,考上了就供自己上大学,没考上就供自己复读。想到未来,小简也有担忧,“其实我都害怕自己变成困在高考里的三年或者五年,但是考不上本科我就得去上班。我还没见过大学,想去看看”。从网上知道计算机专业收入高之后,“大厂”成了小简的憧憬,“年轻人就应该去大城市打拼,大厂的活肯定比拧螺丝轻松,而且挣得多。”她希望自己升入本科后还能再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大厂”工作。她对大城市真实的生存压力、考研的竞争激烈程度一无所知,只是满怀期待地规划着自己走出农村后的未来。
现在,班上仍然有取笑小简的同学。因为小简总是在深夜独自留在教室学习,他们叫她“老鹰”,但小简并不在意,“雌鹰是强者,我喜欢雌鹰”。学校人少了,小简感觉冬天变冷了许多,她准备买一个热水袋,好让自己在走廊上背书时能捂一捂那双总因长冻疮而刺痛的手。背书的间隙,小简喜欢抬头往学校外的区域望去,她希望一年后的自己抬眼看见的,不再是迷蒙雾气中低矮破旧的平房,而是喧嚷热闹的繁城之中,耸立云天的高楼。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简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