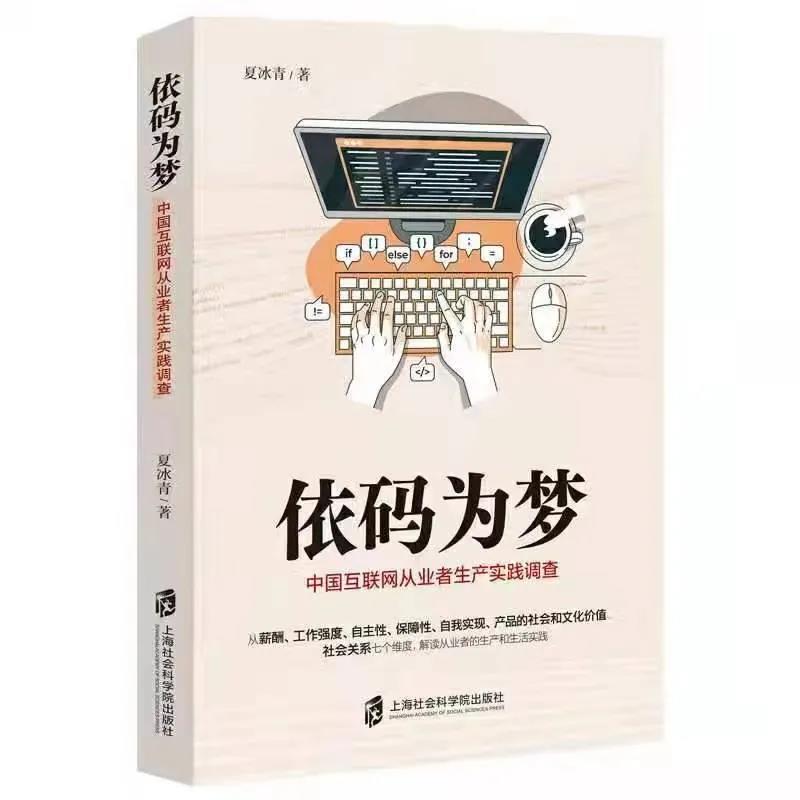
《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
夏冰青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很高兴看到年轻同事夏冰青的《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即将出版。这本著作是冰青十多年田野工作的结晶。作为八零后的年轻学人,冰青回顾了自己成长的经验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她自己也是田野。从自己出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从澳门、伦敦、北京、杭州、深圳、上海、贵州……这个地域的名单还在不断延续,从北上广的中央商务区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她一直在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田野”里摸打滚爬,也一直是我们传播学院田野调查最忙的人。一到假期,她就天南地北地跑,像候鸟一样去追逐她的研究对象。她的口头禅是“得趁着年轻跑得动”。从海外的课堂到中国的田野、中国的课堂,她以奔跑的姿态去追逐自己的思考和理想——思考是方法,理想是动力,也诠释了一位年轻中国传播学人的国际视野、成长轨迹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书稿的田野时间主要集中在2009到2015年,是冰青从澳门大学作为硕士研究生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的田野故事,也是冰青自己的青春成长史。以滚雪球的方式,她先后在2009年、2010年、2011年、2015年多次在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进行调查,甚至想办法以实习生的方式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打”了四个月的工。在互联网企业实习期间,每天下班后晚上整理田野笔记,每两三周把笔记的关键内容翻译成英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自己的两位博士生导师,后者认真批注,解答问题,帮助调整方向。冰青前后积累的田野调查笔记近百万字。这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爆发的关键期,也是世界互联网走向急速大规模市场垄断和金融化的前夜。她聚焦的是这个时期的几乎与她一样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这些从业者五年左右基本上就是互联网产业的一个代际。他们的故事承前启后,冰青的观察对象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数字经济”不可忽略的“前世”。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黄金时期,依“码”为梦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普遍叫做“码农”,或数字劳工,当这个名称开始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时代已经进入新的一页。
冰青希望建立一个互联网从业者的内部动态视角,以勾勒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路线图。在这一点上,她承接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赫思蒙德夫的观点,即从业者对生产实践的主观经验是解读创意产业复杂性的重要视角,也因此接续了导师执意把“创意劳工”从“知识劳工”中单列出来讨论的做法,因为这样才能够“回归到文化产业的特性与本质来凸显其独特生产实践经验”。其实,广义和狭义的文化生产者范畴的划分,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广义的文化生产者强调把文化生产的全链条从业者纳入研究视野——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整体”性视野的体现,也是对产业链条中“弱势者”平等意义的追究,比如出版行业需要关注图书管理员与印刷工人等,数字经济需要关注外卖小哥和数据标注工等——顺便说一句,当下冰青正在进行的田野就是关于数据标注工的研究,期待她的第二部相关著作早日瓜熟蒂落。强调广义文化生产者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暴露出今天热议的“非物质劳动”背后与“物质性劳动”的深刻联系,这一点是今天讨论数字劳动中不可被忽略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狭义的文化生产者研究的意义,相反,强调每一个生产者群体的特殊性才能描绘出整个生产链条之间的关联。事实上,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前提,大处着眼才能小处着手,彼此本来就是辩证的关系。
依靠研究者自己的田野与在场,对从业者主观经验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这样的“质化研究”是一种无法讨巧的笨功夫,也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沉浸式研究。冰青反复研读自己海量的田野笔记,阅读的过程是不断归纳、总结和思考的过程,更是一种需要不断回归自我的反身思考状态:田野就是自我和他者的伦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冰青就学术伦理问题的讨论,是今天中国新传学界不被重视的一环,也是需要获得高光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冰青遭遇的互联网大厂对学术视角的警惕和排斥——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处理学术研究的伦理关系,既是挑战,也是今天中国学术话语生产的一个命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急速变动的大田野,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自我与社会、学术以及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日常教学和科研实践必须回应的问题。冰青曾经把自己在田野中“隐蔽式研究”的伦理困境提交到国际会议讨论,与会者认为与“本土化”的问题及其情境有关。然而,“本土化”挑战正是横亘在中国学人面前的“命运”。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书稿最后结束于冰青对自己课堂的反思。社交媒体时代,传播学院的在校学生越来越多地卷入互联网的内容生产,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反身思考的起点和框架,是批判传播学面对的任务。
在本书中,冰青跟踪的“那些大厂那些人”,是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以一线城市“985”“211”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从业者群体,是这个时代的风向标,是新世代的“白领”阶层,也是判断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等高线。他们与2009年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所揭示的“蚁族”群体正好处于社会的两端,却互相映照,展示出共同存在的共同社会基石。冰青参考并修订了导师赫思蒙德夫关于“创意工作”研究的理论框架,用“薪酬”“工作强度”“自主性”“保障性”“自我实现”“产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和“社会关系”作为描述互联网产业从业者的七个维度。随着从业者寻求“创意自主性”的追求与这个行业的商品化和金融化之间张力的展开,“工作”和“休闲”的边界成为一个问题。产业的发展是内部因素动态形塑的过程,产业的变革反过来又建构从业者的生产实践,冰青试图把这个互动的过程落到从业者个体故事的微观视角,自下而上地回应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宏观图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被热烈讨论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不能真正有效揭示出这些从业者经历的故事,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歧义丛生)的标签,而是把它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分析。
冰青的研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她既体会到这个群体“蓬勃昂扬”的斗志:不知疲倦的奋斗感和兴奋感。那是梦想的力量,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急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它链接着“自我实现”的社会与文化的价值意义。对互助、欢悦感和成就感的分享,是自愿免费加班的重要动力,这种精神通过“加班文化”导引到公司的“利益”链中——它是当下关于“996”争议的前世,它的今生则是“蚂蚁金服”所代表的“财富自由”欢呼最终变成一地鸡毛。关于“996”问题的讨论,批判传播学倾向于揭示背后的剥削机制,这当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更重要的问题却是:为什么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梦想为什么会破碎?冰青描述了这个群体关于员工持股的“迷思”,不可实现的一夕之间“财富自由”,内部深刻的等级歧视链,他们的创意自主性又如何一步步被侵蚀,以及在这个群体之外大量底层的实习生、外包人群和外部培训班所构成的复杂的组织生态——他们构成了这个行业庞大从业者的复杂图谱。
最有意味的或许是冰青对互联网企业从垄断走向金融化之内部逻辑的揭示。2009年到2015年间,互联网“大厂”通过垄断限制新兴企业进入市场。垄断的诉求促使“大厂”不断以投资与收购的方式进行扩张,而不是创新性生产。它们不断蚕食新兴内容领域,在市场中建立屏障,挤压创新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并将失败的风险转嫁给这些新兴企业。这种金融化过程导致“大厂”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倒退,也促使第一批创业者从具有“道德意义”上的生产实践中退出,将注意力转移到融资变现,成为“等待的资本家”。由此,滋养互联网发展的“理想主义”之梦也就走到了尽头。对于新千年第一批互联网的从业者来说,“拿股权,等上市,实现财务自由,离开互联网”成为新选择。至此之后,中国互联网的故事就需要新的演绎方式了。当我们目睹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像鲨鱼一样不断地把梦想、理想、道德、信念、热情、认同、自由、平等非经济的人类生存条件都狂吞下去,并转换成自身盈利的模式,它就逼近了自身资本化的极限。这个极限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故事正在开启。
是的,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最不缺的就是故事。今天,它已经是不落幕的连续剧,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故事的起点。田野决定视野,期待我们的讲述人,不断把新的辽阔田野带到我们面前。


